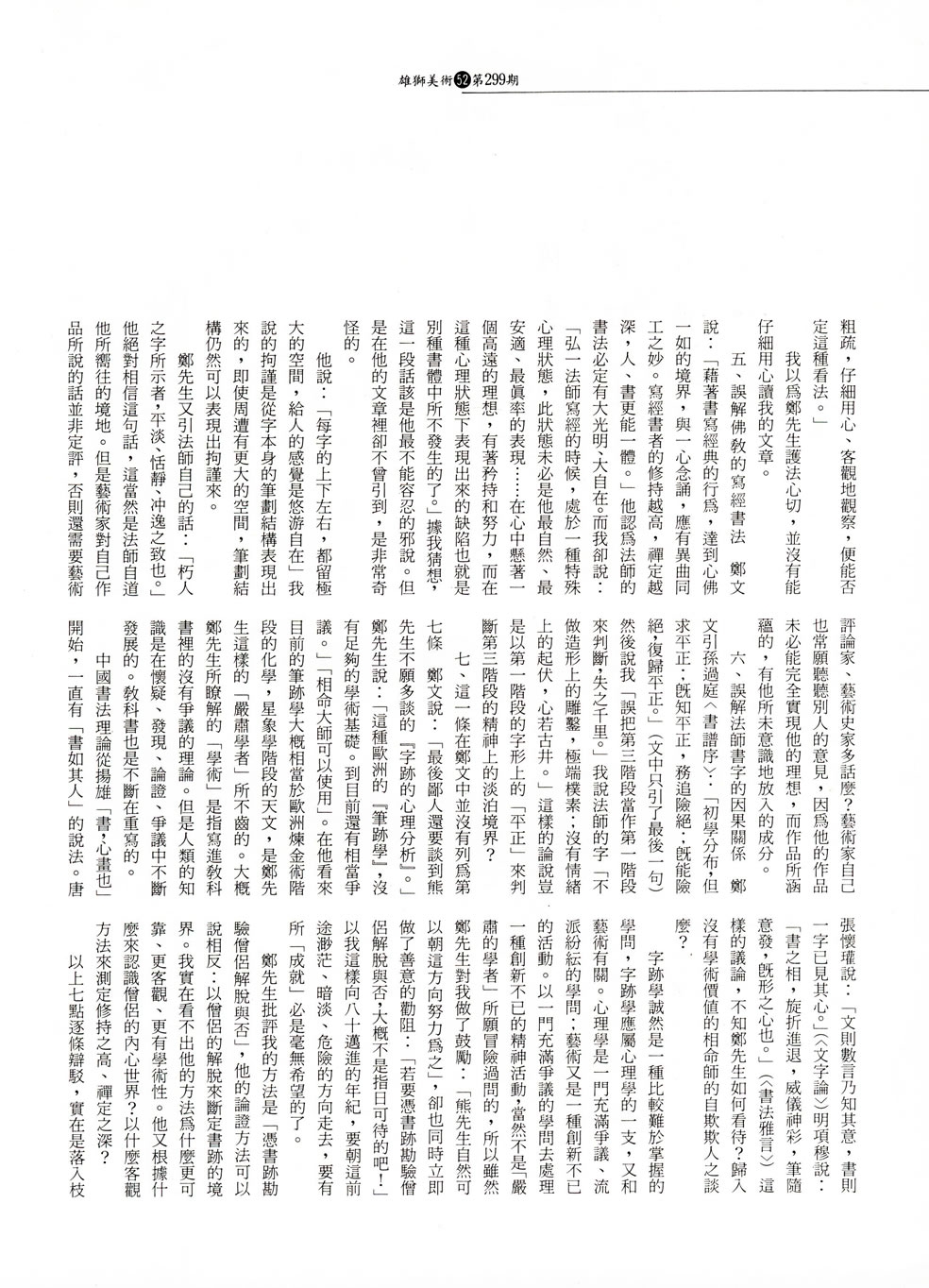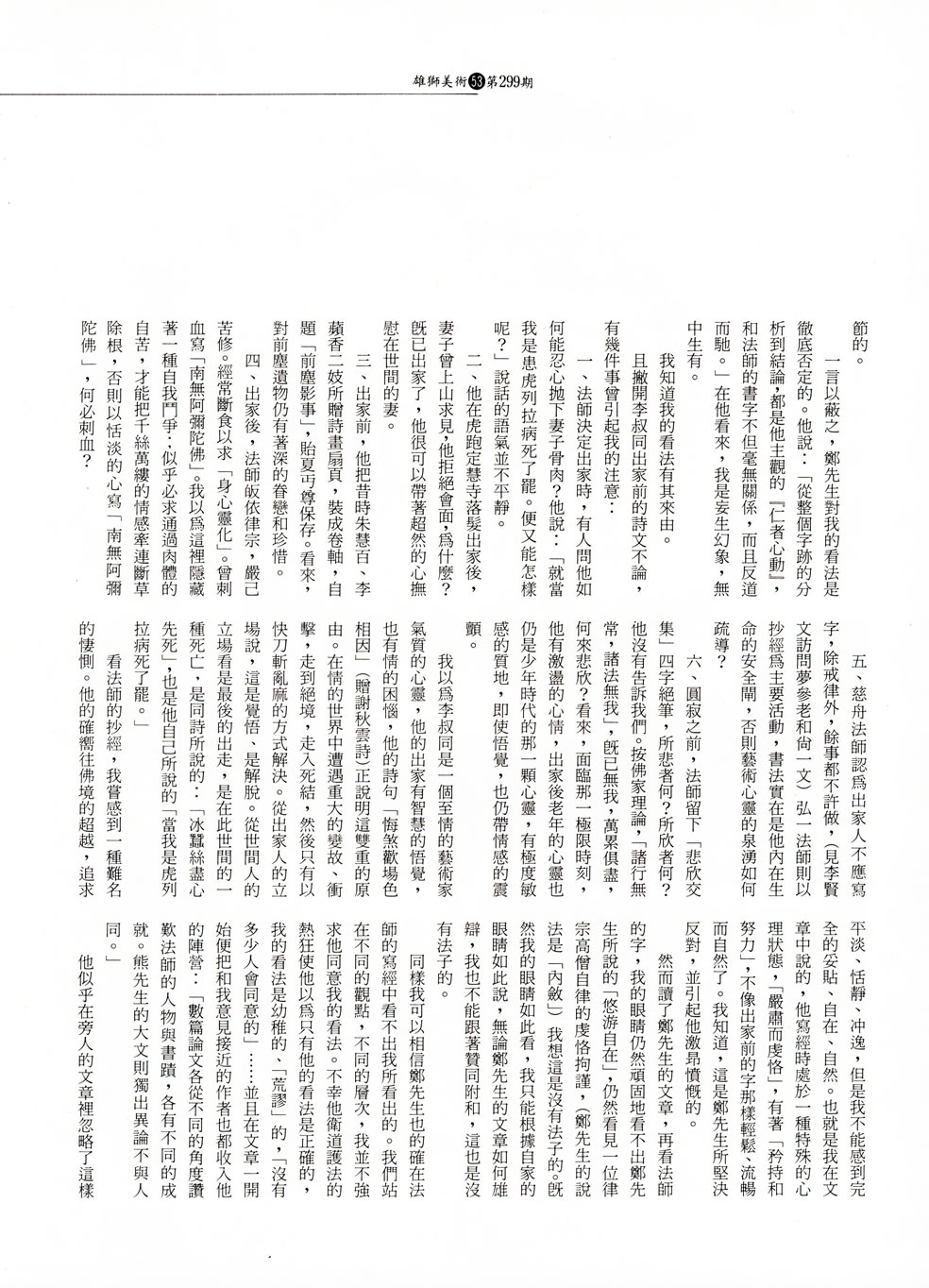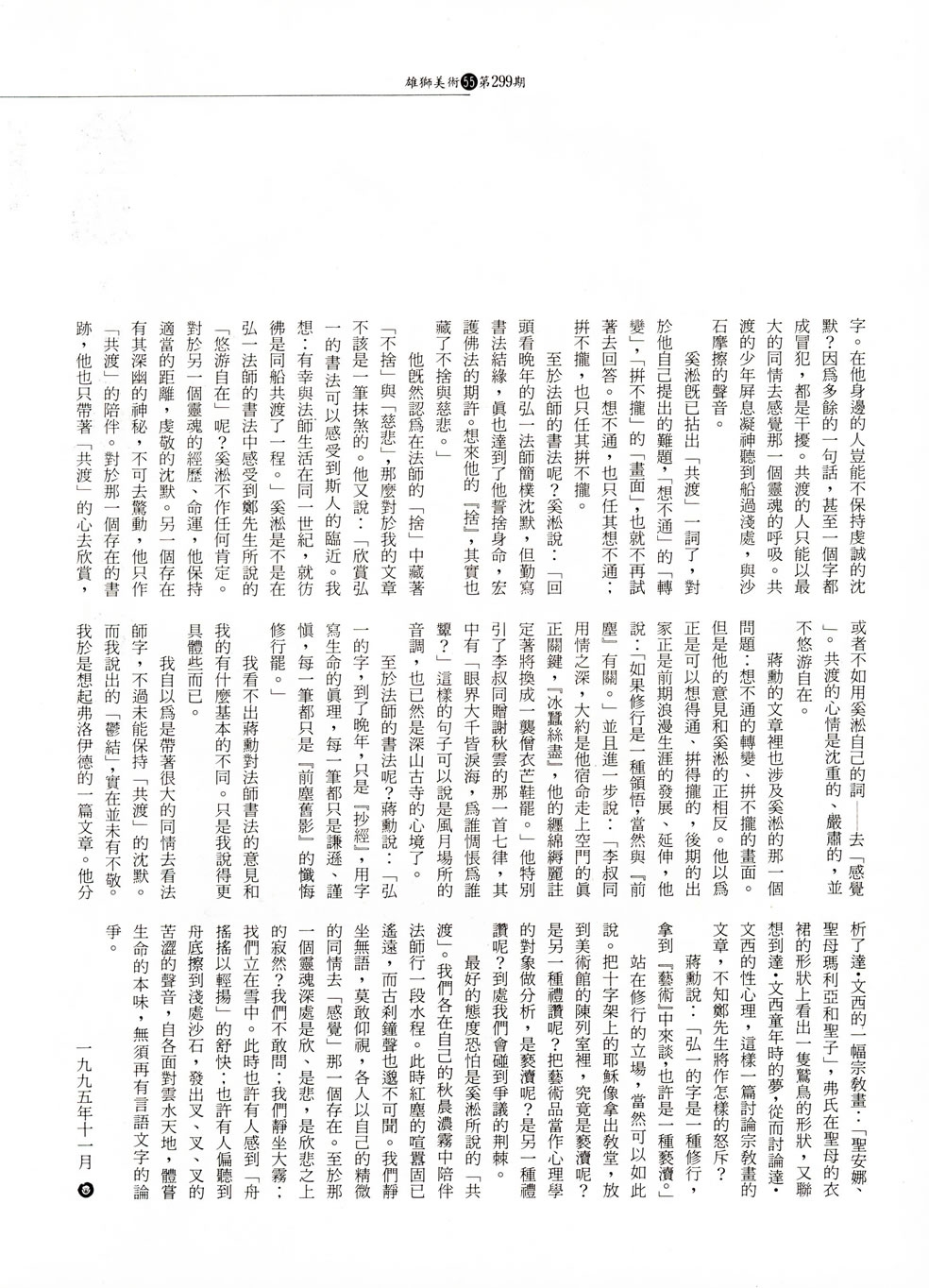1
在雄獅美術弘一法師翰墨專輯中,我發表了一篇〈弘一法師的寫經書風〉。這題目好像在議論法師一生寫經的書法風格,其實著筆時只是從手邊一本法師手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中指出一些特徵,想引人注意。文中雖然對法師寫經時的心理狀態作一些推測,也是帶著同情去觀察,並不敢做武斷的自以為是的肯定,或可說是隨感性的札記吧。
隔了一期便有鄭進發先生發表一篇評論,認為我的那一篇文章「非學術」、「反藝術」,觀察「粗糙」,分析「草率」,結論「荒謬」,運用「三歲小孩」的二分法原始邏輯……我想他的動機大概是好的。他說:「寫經者的修持越高,禪定越深,人、書更能一體。」並引印光法師語:「書經乃欲以凡夫心臟,轉為如來智慧。」在他的心目中,弘一法師已具備如來智慧,凡夫心臟早已轉化,豈有些微渣滓?高僧的書法必定圓潤、澄靜、光明、自在,只合焚香供奉,豈容妄加評論?其態度的認真、徹底、嚴厲,大有金剛怒目,叱咤眾鬼,奮起護法之勢,使我不得不費些筆墨把我們的不同觀點和基本分歧作一些澄清
2
鄭文提出我的六條罪狀,我逐條簡要答覆如下。
一、邏輯問題 因為我的文章中有:「不飄逸,換個說法,即是遲重;不疏放,換個說法,即是拘束。」(「疏」不是錯字。)他於是指出這是兒童邏輯。原文是:「像三歲小孩:『不白,即是黑;不黑,即是白』。」
在這裡二元相排斥的說法,是指兩個不同的理想。「飄逸」和「遲重」之間當然有程度上的相對性,但是作為理想說,則是一維上的兩端,是藝術追求的兩個方向,或向東行,或向西行,是互相排斥的。書家或崇向飄逸疏放,或崇向遲重嚴整,不能同時追求任性自由,又追求矜持守律。因此我說法師的寫經書法傾向遲重嚴整,故不飄逸。我並且把我所瞭解的「逸」的內涵作了解釋。我把法師的書法描寫為「寒簡、淡泊」,但不飄逸,不疏放。這說法實在並無褒貶之意的,而是想把佛家傾向的意境和道家傾向的意境區別開來。
至於認為法師的寫經書法拘謹、遲重,並非我一人的看法,這一點以後還要談到。
二、非學術 鄭文說:「該文的非學術性也表現在他只分析了一件作品,便來概括法師全部寫經書風。」我在文章的開始便言明分析的是一件作品,並未咬死說這是「全部寫經書風」。此外,以為只在一件作品中指出某種特點,便「沒有充分資料」,「說得天花亂墜,也不過是海市蜃樓」,這是說不通的。比如驗血,只要在耳垂上扎一針,取一滴便夠用了,並不必把全身的血都抽出去化驗的。考古家憑一片頭蓋骨,幾枚牙齒,便描述原始人的面貌、體態、年齡、生活狀況……並不因為資料不充分,便不能說話,不能進行學術研究,何況有的研究,是先在理論上計算出結論,再去找證明的資料;或者先直覺地作假設,再去搜集證明的資料。這樣的理論與假設一時可能被認為「海市蜃樓」,但是後來證明是新領域、新大陸。
三、反藝術 我對弘一法師的書法並未作否定的評價,只是指出某類筆法「暗示某種內在鬱結」。鄭先生指為「荒謬得反藝術」。他說:「把這樣一位富有獨創性的畫家(書家)烙上心理有鬱結的印記,這是顛倒之見。」其實「有獨創性」和「心理上有鬱結」並不相矛盾。甚至相反,鬱結可以成為創造的動力。韓愈的「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正是從心理的鬱結不平處看到文藝的起源。西方類似的藝術論,尤其浪漫主義之後,更是普遍,藝術是所謂「苦悶的象徵」。關於藝術的理論很多,但是要把鬱結和藝術對立起來,倒真是「反藝術」的。
四、分析的問題 他把我的字句改寫了,然後說我的「觀察粗糙」。我的原文是「每一個字都斂聚在同樣的長方形空間之中,沒有特別伸舒的長劃……」,意思是指字的外輪廓呈長方形,並不是鄭先生所說「寫在」長方形的「格子」裡。這可以說我表達得不夠清楚,也可以說鄭先生閱讀粗糙。至於我說法師的字「給人以拘謹的感覺」。他認為:「這是熊先生的自由心證……都是他主觀的『仁者心動』,和法師的書字不但毫無關係,而且背道而馳。」直接了當地說,我是閉著眼睛瞎說,但是我卻在專輯中旁人的文章中讀到這樣的話:
「弘一的字……每一筆都只是謙卑、謹慎,每一筆都只是『前塵影事』的懺悔修行吧。」(蔣勳〈血跡久遠〉)
「而細長的字形中,又夾著上寬下窄的內狹(此處疑有誤字)姿態,使人感其謙卑、內斂且拘謹的出家生活」。(李璧苑〈弘一法師出家後的書藝風格〉)
顯然,說法師的字謹慎、拘謹並不是我一個人的看法。蔣勳把這一特徵和「前塵影事」聯繫起來,李璧苑把這一特徵和皈依律宗的事聯繫起來,都是各有所見的。
在鄭先生自己的文章裡亦說到;「但法師的書風,自四十五歲帶有鍾繇風格的寫經之後,漸有素樸、平淡和內斂的趨向。」我看不出此處的「素樸、平淡和內斂」與我提出的「寒簡、淡泊」和「拘謹」有什麼根本的衝突。
至於「須」字的形象究竟表現拘謹呢?表現悠游自在呢?我以為不是運用不粗糙的觀察與不草率的分析所能解決的問題,最好的檢驗方法是自己握筆濡墨去臨寫一番。在寫「須」字的時候親自體會那左邊的三撇所反映的心理。
至於我提出法師的筆法「缺少變化」,也並非貶意的,原文是:「在這裡,無論點、橫、豎、撇……都以同樣的速度,緩緩地、穩穩地去完成。在時間中的節奏是固定的,不受外界的干擾,也無內在的情緒波瀾。像深山佛寺的鐘聲,屬於天體的韻律。」鄭先生在引文之後,便說:「鄙人相信,這說法並沒有多少人會同意。因為只要我們不那麼粗疏,仔細用心、客觀地觀察,便能否定這種看法。」
我以為鄭先生護法心切,並沒有能仔細用心讀我的文章。
五、誤解佛教的寫經書法 鄭文說:「藉著書寫經典的行為,達到心佛一如的境界,與一心念誦,應有異曲同工之妙。寫經書者的修持越高,禪定越深,人、書更能一體。」他認為法師的書法必定有大光明、大自在。而我卻說:「弘一法師寫經的時候,處於一種特殊心理狀態,此狀態未必是他最自然、最安適、最真率的表現……在心中懸著一個高遠的理想,有著矜持和努力,而在這種心理狀態下表現出來的缺陷也就是別種書體中所不發生的了。」據我猜想,這一段話該是他最不能容忍的邪說。但是在他的文章裡卻不曾引到,是非常奇怪的。
他說:「每字的上下左右,都留極大的空間,給人的感覺是悠游自在」我說的拘謹是從字本身的筆劃結構表現出來的,即使周遭有更大的空間,筆劃結構仍然可以表現出拘謹來。
鄭先生又引法師自己的話:「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靜、冲逸之致也。」他絕對相信這句話,這當然是法師自道他所嚮往的境地。但是藝術家對自己作品所說的話並非定評,否則還需要藝術評論家、藝術史家多話麼?藝術家自己也常願聽聽別人的意見,因為他的作品未必能完全實現他的理想,而作品所涵蘊的,有他所未意識地放入的成分。
六、誤解法師書字的因果關係 鄭文引孫過庭〈書譜序〉:「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文中只引了最後一句)然後說我「誤把第三階段當作第一階段來判斷,失之千里。」我說法師的字「不做造形上的雕鑿,極端樸素;沒有情緒上的起伏,心若古井。」這樣的論說豈是以第一階段的字形上的「平正」來判斷第三階段的精神上的淡泊境界?
七、這一條在鄭文中並沒有列為第七條 鄭文說:「最後鄙人還要談到熊先生不願多談的『字跡的心理分析』。」鄭先生說:「這種歐洲的『筆跡學』,沒有足夠的學術基礎。到目前還有相當爭議。」「相命大師可以使用」。在他看來目前的筆跡學大概相當於歐洲煉金術階段的化學,星象學階段的天文,是鄭先生這樣的「嚴肅學者」所不齒的。大概鄭先生所瞭解的「學術」是指寫進教科書裡的沒有爭議的理論。但是人類的知識是在懷疑、發現、論證、爭議中不斷發展的。教科書也是不斷在重寫的。
中國書法理論從揚雄「書,心畫也」開始,一直有「書如其人」的說法。唐張懷瓘說:「文則數言乃知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文字論〉)明項穆說:「書之相,旋折進退,威儀神彩,筆隨意發,既形之心也。」(〈書法雅言〉)這樣的議論,不知鄭先生如何看待?歸入沒有學術價值的相命師的自欺欺人之談麼?
字跡學誠然是一種比較難於掌握的學問,字跡學應屬心理學的一支,又和藝術有關。心理學是一門充滿爭議、流派紛紜的學問;藝術又是一種創新不已的活動。以一門充滿爭議的學問去處理一種創新不已的精神活動,當然不是「嚴肅的學者」所願冒險過問的,所以雖然鄭先生對我做了鼓勵:「熊先生自然可以朝這方向努力為之」,卻也同時立即做了善意的勸阻:「若要憑書跡勘驗僧侶解脫與否,大概不是指日可待的吧!」以我這樣向八十邁進的年紀,要朝這前途渺茫、暗淡、危險的方向走去,要有所「成就」必是毫無希望的了。
鄭先生批評我的方法是「憑書跡勘驗僧侶解脫與否」,他的論證方法可以說相反:以僧侶的解脫來斷定書跡的境界。我實在看不出他的方法為什麼更可靠、更客觀、更有學術性。他又根據什麼來認識僧侶的內心世界?以什麼客觀方法來測定修持之高、禪定之深?
以上七點逐條辯駁,實在是落入枝節的。
一言以蔽之,鄭先生對我的看法是徹底否定的。他說:「從整個字跡的分析到結論,都是他主觀的『仁者心動』,和法師的書字不但毫無關係,而且反道而馳。」在他看來,我是妄生幻象,無中生有。
我知道我的看法有其來由。
且撇開李叔同出家前的詩文不論,有幾件事曾引起我的注意:
一、法師決定出家時,有人問他如何能忍心拋下妻子骨肉?他說:「就當我是患虎列拉病死了罷。便又能怎樣呢?」說話的語氣並不平靜。
二、他在虎跑定慧寺落髮出家後,妻子曾上山求見,他拒絕會面,為什麼?既已出家了,他很可以帶著超然的心撫慰在世間的妻。
三、出家前,他把昔時朱慧百、李蘋香二妓所贈詩畫扇頁,裝成卷軸,自題「前塵影事」,貽夏丏尊保存。看來,對前塵遺物仍有著深的眷戀和珍惜。
四、出家後,法師皈依律宗,嚴己苦修。經常斷食以求「身心靈化」。曾刺血寫「南無阿彌陀佛」。我以為這裡隱藏著一種自我鬥爭;似乎必求通過肉體的自苦,才能把千絲萬縷的情感牽連斷草除根,否則以恬淡的心寫「南無阿彌陀佛」,何必刺血?
五、慈舟法師認為出家人不應寫字,除戒律外,餘事都不許做,(見李賢文訪問夢參老和尚一文)弘一法師則以抄經為主要活動,書法實在是他內在生命的安全閘,否則藝術心靈的泉湧如何疏導?
六、圓寂之前,法師留下「悲欣交集」四字絕筆,所悲者何?所欣者何?他沒有告訴我們。按佛家理論,「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既已無我,萬累俱盡,何來悲欣?看來,面臨那一極限時刻,他有激盪的心情,出家後老年的心靈也仍是少年時代的那一顆心靈,有極度敏感的質地,即使悟覺,也仍帶情感的震顫。
我以為李叔同是一個至情的藝術家氣質的心靈,他的出家有智慧的悟覺,也有情的困惱,他的詩句「悔煞歡場色相因」(贈謝秋雲詩)正說明這雙重的原由。在情的世界中遭遇重大的變故、衝擊,走到絕境,走入死結,然後只有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解決。從出家人的立場說,這是覺悟、是解脫。從世間人的立場看是最後的出走,是在此世間的一種死亡,是同詩所說的:「冰蠶絲盡心先死」,也是他自己所說的「當我是虎列拉病死了罷。」
看法師的抄經,我嘗感到一種難名的悽惻。他的確嚮往佛境的超越,追求平淡、恬靜、冲逸,但是我不能感到完全的妥貼、自在、自然。也就是我在文章中說的,他寫經時處於一種特殊的心理狀態,「嚴肅而虔恪」,有著「矜持和努力」,不像出家前的字那樣輕鬆、流暢而自然了。我知道,這是鄭先生所堅決反對,並引起他激昂憤慨的。
然而讀了鄭先生的文章,再看法師的字,我的眼睛仍然頑固地看不出鄭先生所說的「悠游自在」,仍然看見一位律宗高僧自律的虔恪拘謹,(鄭先生的說法是「內斂」)我想這是沒有法子的。既然我的眼睛如此看,我只能根據自家的眼睛如此說,無論鄭先生的文章如何雄辯,我也不能跟著贊同附和,這也是沒有法子的。
同樣我可以相信鄭先生也的確在法師的寫經中看不出我所看出的。我們站在不同的觀點,不同的層次,我並不強求他同意我的看法。不幸他衛道護法的熱狂使他以為只有他的看法是正確的,我的看法是幼稚的、「荒謬」的,「沒有多少人會同意的」……並且在文章一開始便把和我意見接近的作者也都收入他的陣營:「數篇論文各從不同的角度讚歎法師的人物與書蹟,各有不同的成就。熊先生的大文則獨出異論不與人同。」
他似乎在旁人的文章裡忽略了這樣的話了:
「弘一的字,到了晚年……每一筆都只是謙遜、謹慎、每一筆都只是『前塵影事』的懺悔修行吧。」(蔣勳文)
「……出家後,卻仍然是非常『儒家』的。」(杜忠誥文)
「而細長的字形中…使人感其謙卑、內斂且拘謹的出家生活……」(李璧苑文之第二篇)
3
我把雄獅的專輯重新檢出,把有關的幾篇文章又讀了。
第一篇是奚淞的。這第二遍的閱讀給我很大的啟發。在這一點上,我要感謝鄭先生,是他逼我再讀幾篇文章的。
奚淞也把李叔同削髮為僧看為一件很不平常的事,他認為難於理解:
「早歲倡新劇,開中國畫裸體模特兒之風,以西洋音樂入曲,光彩四射的一代才子,如何竟遁入極重簡苦的佛教律宗境界,以唸佛往生為所至盼,其中的轉變,就不是那麼容易想通的了。」
又說:「想像李叔同曾經在日本演出過這樣動情的戲劇角色,再想他十年後在杭州虎跑寺的削髮成僧模樣,就像天南地北,拼不攏來的畫面。」
這「轉變」,他想不通;這「畫面」,他拼不攏。所以他說「對後世人如我,與其說弘一法師是可理解的,不若說是可感覺的一種存在。」
如何去感覺呢?那是透過六十五年前一個少年,李芳遠,在一個秋晨送別法師的經驗。那一段文章,無論是奚淞自己的,或者他引李芳遠的,都極值得玩味。我實在想大段錄下來,可惜太長了,這裡只引最重要的一節,李芳遠在江霧中見到孤帆,舟中坐著六十一歲的法師,瘦老如蒼松,正在驚怔,法師微笑起立,合十唸一句:「阿彌陀佛」。
「這聲音清冷輕快,使我全身發抖,莫敢仰視」。
「雖然在先曾想出好多事,備作談話資料,可是到那境界,卻都煙消雲散了……弘一法師更閉了眼睛,微動著口唇,我知道他在唸佛,更不好打擾……唯有靜坐凝神地聽著船過淺處,與石子相擦發出叉、叉、叉的聲音。」
兩人沒有對話,法師「除勸唸佛,速得了脫生死外,別無他語。」奚淞透過李芳遠的經驗「感覺」到了什麼呢?他說:
「讀李芳遠的〈送別晚晴老人〉一文,使相隔半世紀的我,似也在秋日江上與法師同舟共渡,靜聽了舟行摩擦淺渚的聲音。」
他拈出了「共渡」一詞來形容他的「感覺」,並且放入文章的題目〈秋江共渡〉。法師的心靈秘不可測。他的話雖少,但是使少年「全身發抖,莫敢仰視」。其內心有割捨之痛,有解脫之欣,靈魂遭受的熬煎,只獨自承擔,不吐露一個字。在他身邊的人豈能不保持虔誠的沈默?因為多餘的一句話,甚至一個字都成冒犯,都是干擾。共渡的人只能以最大的同情去感覺那一個靈魂的呼吸。共渡的少年屏息凝神聽到船過淺處,與沙石摩擦的聲音。
奚淞既已拈出「共渡」一詞了,對於他自己提出的難題,「想不通」的「轉變」,「拼不攏」的「畫面」,也就不再試著去回答。想不通,也只任其想不通;拼不攏,也只任其拼不攏。
至於法師的書法呢?奚淞說:「回頭看晚年的弘一法師簡樸沈默,但勤寫書法結緣,真也達到了他誓捨身命,宏護佛法的期許。想來他的『捨』,其實也藏了不捨與慈悲。」
他既然認為在法師的「捨」中藏著「不捨」與「慈悲」,那麼對於我的文章不該是一筆抹煞的。他又說:「欣賞弘一的書法可以感受到斯人的臨近。我想:有幸與法師生活在同一世紀,就彷彿是同船共渡了一程。」奚淞是不是在弘一法師的書法中感受到鄭先生所說的「悠游自在」呢?奚淞不作任何肯定。對於另一個靈魂的經歷、命運,他保持適當的距離,虔敬的沈默。另一個存在有其深幽的神秘,不可去驚動,他只作「共渡」的陪伴。對於那一個存在的書跡,他也只帶著「共渡」的心去欣賞,或者不如用奚淞自己的詞——去「感覺」。共渡的心情是沈重的、嚴肅的,並不悠游自在。
蔣勳的文章裡也涉及奚淞的那一個問題:想不通的轉變、拼不攏的畫面。但是他的意見和奚淞的正相反。他以為正是可以想得通、拼得攏的,後期的出家正是前期浪漫生涯的發展、延伸,他說:「如果修行是一種領悟,當然與『前塵』有關。」並且進一步說:「李叔同用情之深,大約是他宿命走上空門的真正關鍵,『冰蠶絲盡』,他的纏綿縟麗註定著將換成一襲僧衣芒鞋罷。」他特別引了李叔同贈謝秋雲的那一首七律,其中有「眼界大千皆淚海,為誰惆悵為誰顰?」這樣的句子可以說是風月場所的音調,也已然是深山古寺的心境了。
至於法師的書法呢?蔣勳說:「弘一的字,到了晚年,只是『抄經』,用字寫生命的真理,每一筆都只是謙遜、謹慎,每一筆都只是『前塵舊影』的懺悔修行罷。」
我看不出蔣勳對法師書法的意見和我的有什麼基本的不同。只是我說得更具體些而已。
我自以為是帶著很大的同情去看法師字,不過未能保持「共渡」的沈默。而我說出的「鬱結」,實在並未有不敬。我於是想起弗洛伊德的一篇文章。他分析了達.文西的一幅宗教畫:「聖安娜、聖母瑪利亞和聖子」,弗氏在聖母的衣裙的形狀上看出一隻鷲鳥的形狀,又聯想到達.文西童年時的夢,從而討論達.文西的性心理,這樣一篇討論宗教畫的文章,不知鄭先生將作怎樣的怒斥?
蔣勳說:「弘一的字是一種修行,拿到『藝術』中來談,也許是一種褻瀆。」
站在修行的立場,當然可以如此說。把十字架上的耶穌像拿出教堂,放到美術館的陳列室裡,究竟是褻瀆呢?是另一種禮讚呢?把藝術品當作心理學的對象做分析,是褻瀆呢?是另一種禮讚呢?到處我們會碰到爭議的荊棘。
最好的態度恐怕是奚淞所說的「共渡」。我們各在自己的秋晨濃霧中陪伴法師行一段水程。此時紅塵的喧囂固已遙遠,而古剎鐘聲也邈不可聞。我們靜坐無語,莫敢仰視,各人以自己的精微的同情去「感覺」那一個存在。至於那一個靈魂深處是欣、是悲,是欣悲之上的寂然?我們不敢問;我們靜坐大霧;我們立在雪中。此時也許有人感到「舟搖搖以輕揚」的舒快;也許有人偏聽到舟底擦到淺處沙石,發出叉、叉、叉的苦澀的聲音,自各面對雲水天地,體嘗生命的本味,無須再有言語文字的論爭。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