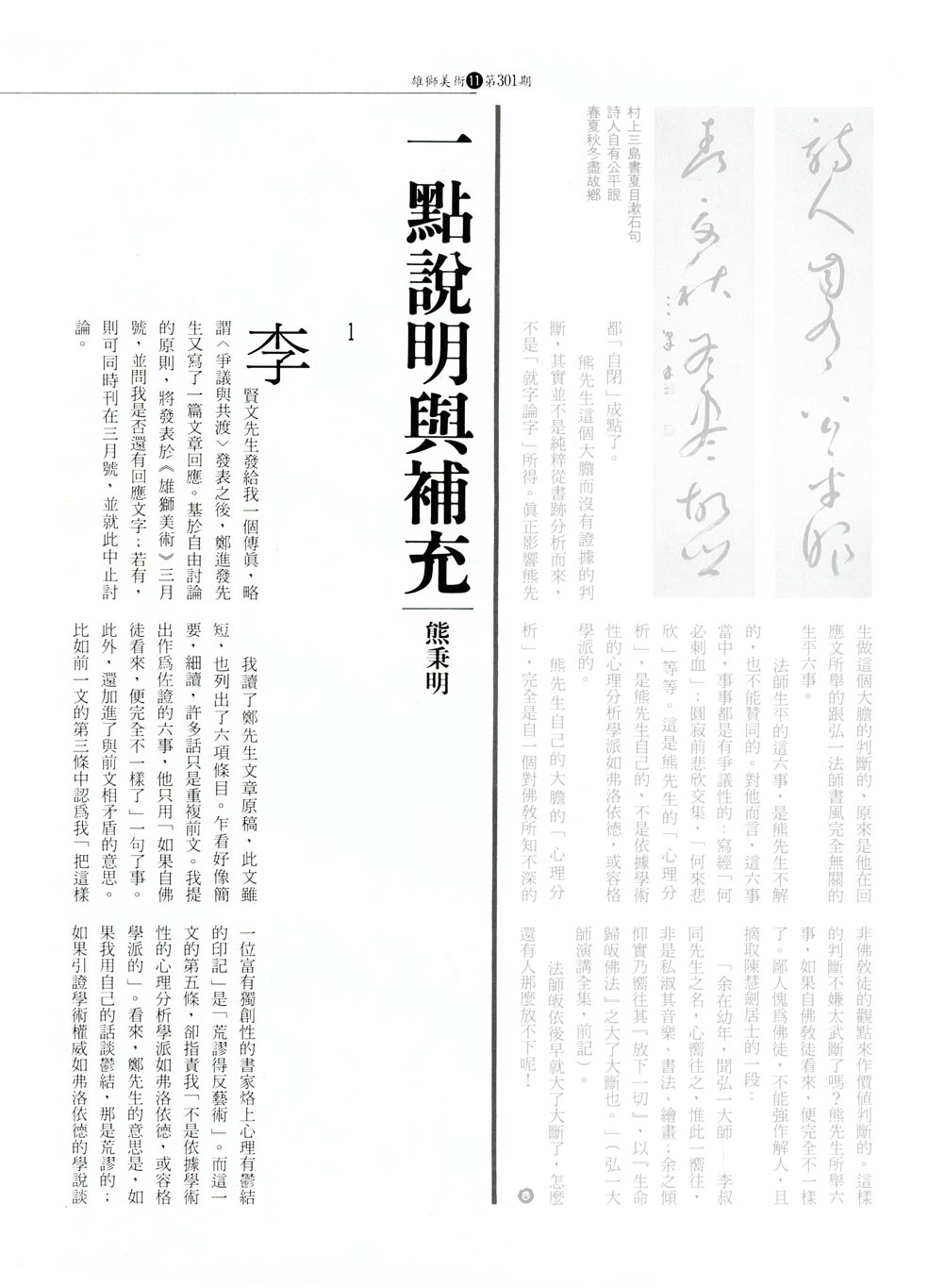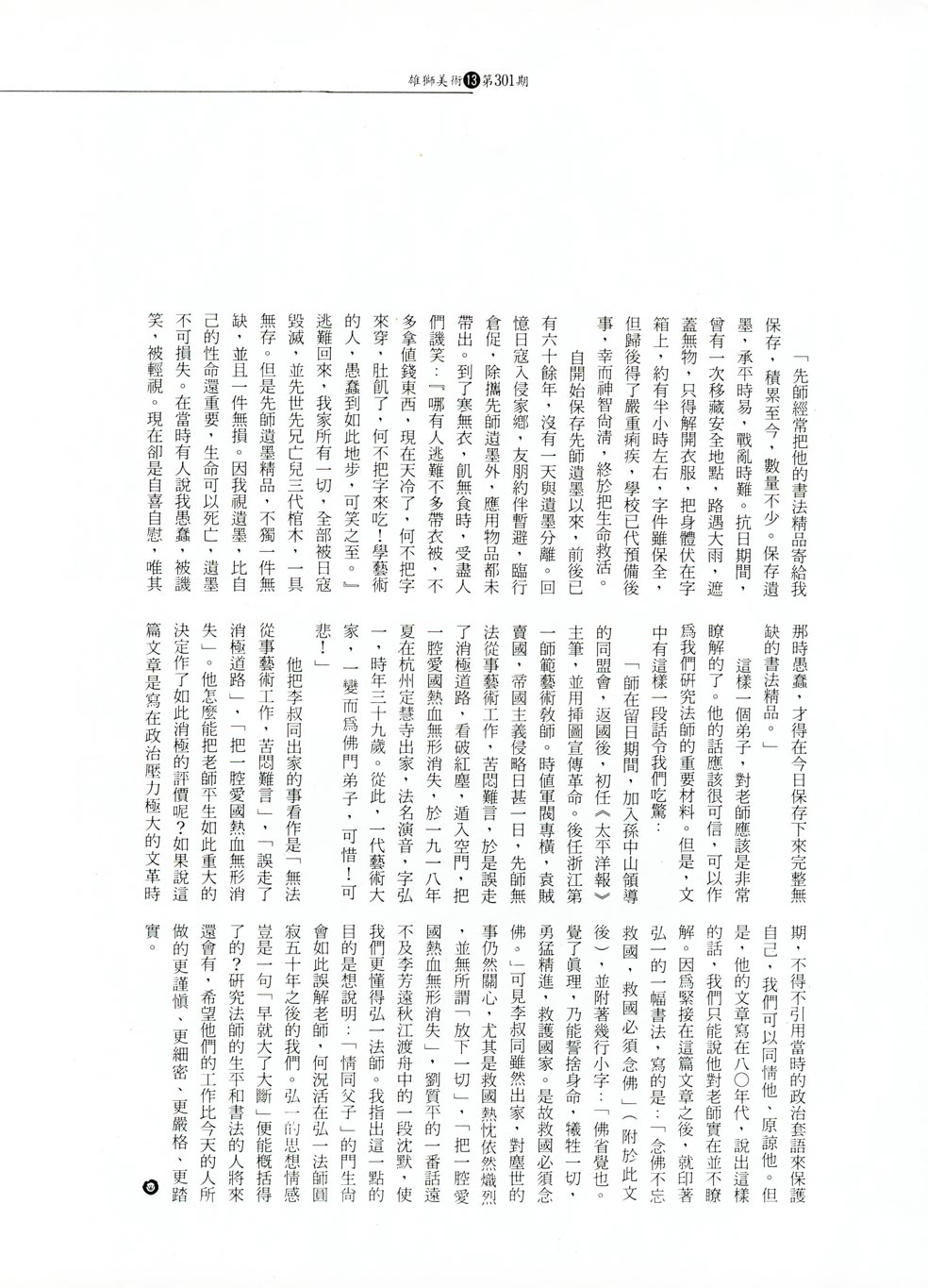1
李賢文先生發給我一個傳真,略謂〈爭議與共渡〉發表之後,鄭進發先生又寫了一篇文章回應。基於自由討論的原則,將發表於《雄獅美術》三月號,並問我是否還有回應文字;若有,則可同時刊在三月號,並就此中止討論。
我讀了鄭先生文章原稿,此文雖短,也列出了六項條目。乍看好像簡要,細讀,許多話只是重複前文。我提出作為佐證的六事,他只用「如果自佛徒看來,便完全不一樣了」一句了事。此外,還加進了與前文相矛盾的意思。比如前一文的第三條中認為我「把這樣一位富有獨創性的書家烙上心理有鬱結的印記」是「荒謬得反藝術」。而這一文的第五條,卻指責我「不是依據學術性的心理分析學派如弗洛依德,或容格學派的」。看來,鄭先生的意思是,如果我用自己的話談鬱結,那是荒謬的;如果引證學術權威如弗洛依德的學說談鬱結,那麼就有根有據,站得住了。現在讓我們看看弗洛依德是怎樣談鬱結的。弗洛依德認為,人有强烈的本能欲求,在現實生活中,不能得到滿足的時候,感到失望痛苦,可借藝術創作得到宣洩和昇華。弗洛依德所指的本能欲求,主要是性欲求,他稱之為「力比多」(Libido)。藝術創造就是藝術家受壓抑的「力比多」得到轉化、提升的活動。所以有人稱他的學說為「泛性論」。鄭先生既有弘一法師「早已大了大斷」的看法,怎可能再提出弗洛依德的理論,容忍「泛性論」的精神病理學觀點來討論弘一的書法?豈不自相矛盾?至於容格,他說過這樣的話:「真正的藝術是一種創造,而所有創造總是超越於一切理論的。這也就是我為什麼總要對藝術初學者說:『儘管你可以盡你的能力去學習理論,但是要記住,當你接觸到活生生的靈魂的奇蹟的時候,你就應當把理論丟在一邊,除了你自己個人的創造力之外,理論是無能為力的。』」(容格和貝恩斯著《獻給分析心理學》)。可見,鄭先生雖然勸告別人用容格的理論來分析藝術作品,容格自己並不贊同。
容格並不認為有一套現成的藝術理論,像百寶丹,可以用來解釋一切藝術創造。面對「活生生的靈魂的奇蹟」,還要運用自己的敏感和思想。弗洛依德的學說雖然深刻地影響了近代思潮,但是就在他在世的時候,已經有了紛紛的異議。他的學生的一代如阿德勒(Adler,1870–1937)、蘭克(Rank,1884–1939)等人,還有容格,都在他的啟發下創造了不同的理論,精神分析至今是一門流派眾多而門戶之見甚深的學科。西方各國也因文化傳統和民族性的不同各有不同的傾向。「學術性」並不指不可動搖、沒有爭議,可以照搬照抄的經典的權威性。
其他問題就不再贅述。我們對「學術」的理解既然如此不同,而對生命的體驗和反思距離更遠,繼續寫下去,不可能得到什麼積極的結果。
2
在寄出〈爭議與共渡〉之後,看到一份資料,覺得值得發表出來。此文在台灣大概很難見到,所以較長地作了摘錄,以供《雄獅美術》的讀者參考。
北京出版的《中國書法》雜誌在一九八六年第四期刊出有關弘一法師書法的三篇文章。其中第一篇〈弘一法師遺墨保存及其生活回憶〉註明是「劉質平遺作」。據編者按,劉是弘一法師的得意門生。文章大概寫在八〇年代初,在一九八六年之前。文章末尾說他多年保存老師的作品,現在年已七十有九,年老多病,將不久於世,應該結束保管責任,把全部收藏獻給國家。文章寫到他和弘一交往的情誼和他收藏弘一書法的原委:
「我與先師,名雖師生,情同父子。我家祖上四代都是窮苦出身,我於民國初年入杭州師範讀書(學、雜、書籍、飯費全免),從先師課外研究音樂五年。畢業後,先師又培養我東渡留日,所有費用由師資助,而師入山後直至去世的二十五年間,一切生活費用都由我供給,從未間斷。」
他對老師的書法作品愛惜如命,有具體的追述:
「先師經常把他的書法精品寄給我保存,積累至今,數量不少。保存遺墨,承平時易,戰亂時難。抗日期間,曾有一次移藏安全地點,路遇大雨,遮蓋無物,只得解開衣服,把身體伏在字箱上,約有半小時左右,字件雖保全,但歸後得了嚴重痢疾,學校已代預備後事,幸而神智尚清,終於把生命救活。
自開始保存先師遺墨以來,前後已有六十餘年,沒有一天與遺墨分離。回憶日寇入侵家鄉,友朋約伴暫避,臨行倉促,除攜先師遺墨外,應用物品都未帶出。到了寒無衣,飢無食時,受盡人們譏笑:『哪有人逃難不多帶衣被,不多拿值錢東西,現在天冷了,何不把字來穿,肚飢了,何不把字來吃!學藝術的人,愚蠢到如此地步,可笑之至。』逃難回來,我家所有一切,全部被日寇毀滅,並先世先兄亡兒三代棺木,一具無存。但是先師遺墨精品,不獨一件無缺,並且一件無損。因我視遺墨,比自己的性命還重要,生命可以死亡,遺墨不可損失。在當時有人說我愚蠢,被譏笑,被輕視。現在卻是自喜自慰,唯其那時愚蠢,才得在今日保存下來完整無缺的書法精品。」
這樣一個弟子,對老師應該是非常瞭解的了。他的話應該很可信,可以作為我們研究法師的重要材料。但是,文中有這樣一段話令我們吃驚:
「師在留日期間,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返國後,初任《太平洋報》主筆,並用插圖宣傳革命。後任浙江第一師範藝術教師。時值軍閥專橫,袁賊賣國,帝國主義侵略日甚一日,先師無法從事藝術工作,苦悶難言,於是誤走了消極道路,看破紅塵,遁入空門,把一腔愛國熱血無形消失,於一九一八年夏在杭州定慧寺出家,法名演音,字弘一,時年三十九歲。從此,一代藝術大家,一變而為佛門弟子,可惜!可悲!」
他把李叔同出家的事看作是「無法從事藝術工作,苦悶難言」,「誤走了消極道路」,「把一腔愛國熱血無形消失」。他怎麼能把老師平生如此重大的決定作了如此消極的評價呢?如果說這篇文章是寫在政治壓力極大的文革時期,不得不引用當時的政治套語來保護自己,我們可以同情他、原諒他。但是,他的文章寫在八〇年代,說出這樣的話,我們只能說他對老師實在並不瞭解。因為緊接在這篇文章之後,就印著弘一的一幅書法,寫的是:「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附於此文後),並附著幾行小字:「佛省覺也。覺了真理,乃能誓捨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是故救國必須念佛。」可見李叔同雖然出家,對塵世的事仍然關心,尤其是救國熱忱依然熾烈,並無所謂「放下一切」,「把一腔愛國熱血無形消失」,劉質平的一番話遠不及李芳遠秋江渡舟中的一段沈默,使我們更懂得弘一法師。我指出這一點的目的是想說明:「情同父子」的門生尚會如此誤解老師,何況活在弘一法師圓寂五十年之後的我們。弘一的思想情感豈是一句「早就大了大斷」便能概括得了的?研究法師的生平和書法的人將來還會有,希望他們的工作比今天的人所做的更謹慎、更細密、更嚴格、更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