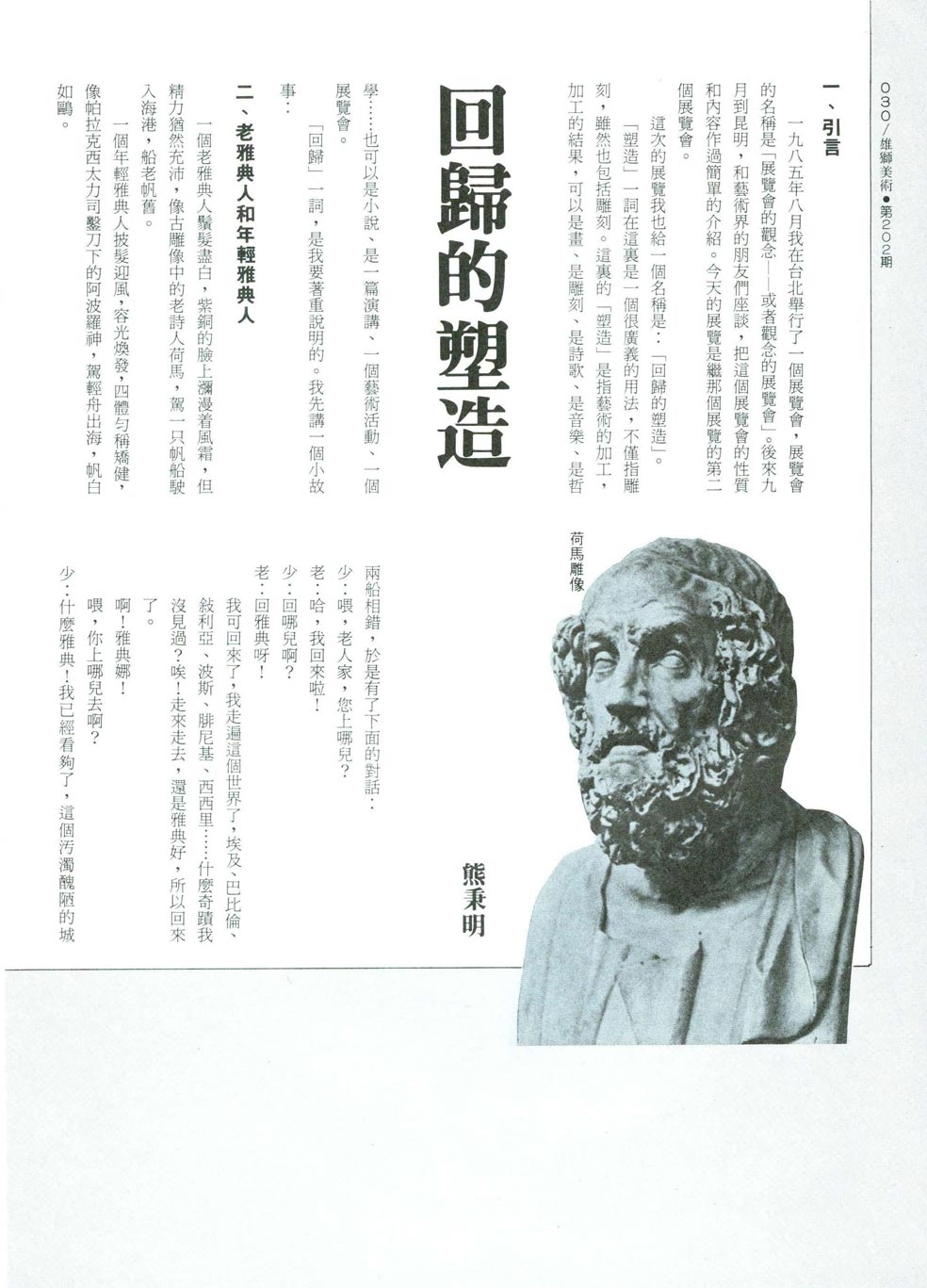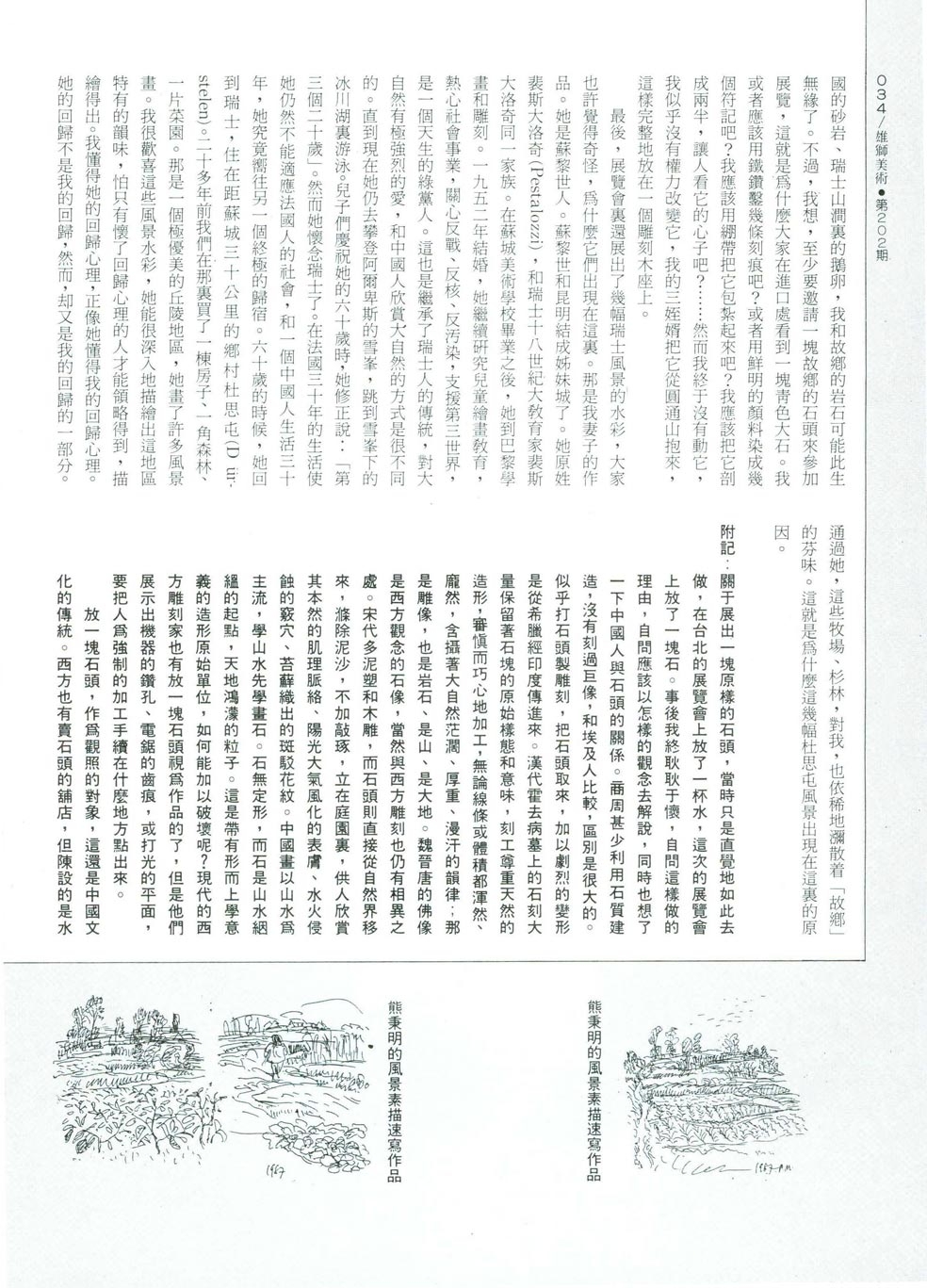一、引言
一九八五年八月我在台北舉行了一個展覽會,展覽會的名稱是「展覽會的觀念——或者觀念的展覽會」。後來九月到昆明,和藝術界的朋友們座談,把這個展覽會的性質和內容作過簡單的介紹。今天的展覽是繼那個展覽的第二個展覽會。
這次的展覽我也給一個名稱是:「回歸的塑造」。
「塑造」一詞在這裡是一個很廣義的用法,不僅指雕刻,雖然也包括雕刻。這裡的「塑造」是指藝術的加工,加工的結果,可以是畫、是雕刻、是詩歌、是音樂、是哲學……也可以是小說、是一篇演講、一個藝術活動、一個展覽會。
「回歸」一詞,是我要著重說明的。我先講一個小故事:
二、老雅典人和年輕雅典人
一個老雅典人鬚髮盡白,紫銅的臉上瀰漫著風霜,但精力猶然充沛,像古雕像中的老詩人荷馬,駕一只帆船駛入海港,船老帆舊。
一個年輕雅典人披髮迎風,容光煥發,四體勻稱矯健,像帕拉克西太力司鑿刀下的阿波羅神,駕輕舟出海,帆白如鷗。兩船相錯,於是有了下面的對話:
少:喂,老人家,您上哪兒?
老:哈,我回來啦!
少:回哪兒啊?
老:回雅典呀!
我可回來了,我走遍這個世界了,埃及、巴比倫、敘利亞、波斯、腓尼基、西西里……什麼奇蹟我沒見過?唉!走來走去,還是雅典好,所以回來了。
啊!雅典娜!
喂,你上哪兒去啊?
少:什麼雅典!我已經看夠了,這個污濁醜陋的城市,市儈和官僚統治的城市。你聽說了吧,把蘇格拉底處了死刑了……這樣的地方我實在住不下去了,到開羅的街頭作流浪漢、作乞丐,我也要去了……你回雅典?
老、少(同時指著對方喊):你瘋了!
在愛琴海的暖風中,深藍的浪濤激盪中,兩只小船迅速地離遠。
附記:這是畫家司徒立講給我的一個故事,我不知道他是從哪裡聽來或者看來的,我覺得極有意思,很感謝他,特別註在這裡。最近問一個希臘女建築師,可知道這個故事。她也不知道,卻說很像一個希臘故事。
三、遠行與回歸
在這裡,我們看到兩千多年前的所謂「代溝」。近數十年來,由於社會變化的加速,不僅父子之間有代溝,就兄弟姊妹之間,相差不過十年、五年,精神面貌已有了差距,但是最基本的代溝究竟還是年輕人和老年人之間的。
我們知道生命需要一個活動的空間,在成長過程中,生命所需要的空間不斷擴大。未降生之時,胎兒的空間是母體的子宮;既生之後,嬰孩生活在母懷裡、搖籃裡;到了會爬行、會扶著牆走,就要在室內轉動;會走路,就要跨出門檻,到庭院裡去;再大,就要上街、去公園、到學校、到外婆家;再大,他的活動範圍是這個城市;再大,他將去別的城市、別的國家。然而,到了一個年紀,這變化又向相反的方向進行,他的活動範圍逐漸縮小。他的體力先不允許他再四方奔走,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適應力和好奇心也漸減退,眼睛已看不遠,聽話也已模糊。在這個世界上他會覺得有一個地方是他最喜歡的,在那裡他可以舒適地安頓下來,徜徉,終老於斯。這大概是他的家鄉,他的生命長途的起點。童年的記憶給他以強烈的召喚,他最先學會適應的氣候、陽光、土壤……沉澱在他記憶底層的,慢慢醒來。
這兩種心理我們可以分別稱作:「遠行心理」,年輕雅典人的心理;和「回歸心理」,老雅典人的心理。中國常語所說的「志在四方」和「葉落歸根」。
國內施行開放政策後,很多年輕人激烈地想著到國外去,這是可以理解的。在座的都是文藝工作者,當中有的很年輕,必定盼望看別種顏色的天空、別種儀態的山,看未曾見過的大平原、大河和海洋,看別個民族的畫、別個時代的雕刻、別的城市的建築……開始和外面的世界有了接觸。你們想看新的、現代的藝術、世界上另一些年輕人的創造和嘗試,我不會向你們喊:「你瘋了!」但是有一點我願提醒大家,看別種顏色的天空,最後還是為了畫出自己的天空來。因為看了別樣的天空,你才能更敏銳地辨出這裡的天空的特色,才會更深入、更細膩地繪出這裡的天空。我祝福你們都能有機會遠行,並且最後歸來,作出自己心裡要畫的畫。而這心裡要畫的種種形與色是和故土的種種形與色細細密織在一起的。
國內施行開放政策後,使很多流落在海外的中國人迫切地想著回來,每年成千成萬地回來,扶老携幼地回來,我想你們也不會向他們喊:「你瘋了!」
我自己在西方住了四十年,回來過四次,這是第五次。我記得第二次是在一九七九年,回雲南那是第一次。老朋友王以申、蔣萬華、羅丕焯幾位陪我去彌勒縣,一直到了我的老家息宰村。進到竹園壩子(在雲南稱盆地為「壩子」),看到盤龍江、西山、甘蔗田、水牛、古村……我有一種非常奇異的感覺,彷彿細胞裡、骨髓裡含藏著那地方的什麼原料,它們和那裡的土壤、大氣、水份之間有著吸引、共鳴,而互相召喚。我的細胞裡、腦灰質裡儲存著的什麼遙遠的記憶資料都猛地甦醒……
但是,以前幾次的回來,多少總類似一般歸僑的還鄉,以旅遊方式在國內各地參觀訪問,到了自己本鄉雖然有特別的激動,但終只是被列入觀光日程中的一個項目。這次我完全是為了回故鄉而回來。不曾到其他城市,也不再去別的城市。加強這次「回歸」的感覺還有別的一些原因。五十年前,整整五十年前,一九三七年,我的父親辭去北京清華大學數學系的教授職,回昆明任雲南大學校長,在他的生命中,那曾是一個很重大、很費考慮的決定。他常對我們說:「為桑梓服務。」我的一個弟弟沒有忘記這句話,在長沙工作多年後,他請求調回昆明,今年得到批准,到雲南工學院工作,並且接了老母回來。我的母親久居北京之後,以九十四的高齡,坐了三天三夜火車從北京到了昆明。所以我這次回來,不但是回到故鄉,而且是回到回到故鄉的母親的身邊,回到真真實實的母土。
四、鐵雕和展覽
根據觀念藝術的觀點,藝術與生活應該打成一片,是一回事。藝術在生活上加工,生活因藝術取得形式。所以我把這一次的回歸加工為「回歸的塑造」。
我帶一件雕塑送給故鄉。這是一座「鶴」,展翅將飛的鶴。說它嚮往遠山長水,欲將遠行也可以;說它懷想舊林故淵,欲將回歸也可以。大家知道,法國詩人波特萊爾有一首詩題為「旅行的邀約」,這鶴對一些人說是「遠行的邀約」,對另外一些人說則是「歸來的邀約」。
我把贈雕塑的意思告訴畫家姚鍾華先生,經他接洽,政協表示願意接受,將來放置在目前正在興建的民主大樓之前,放大焊製的任務由雲南重機廠承擔。
其次我舉行這個小的展覽會。
展覽會的第一部分是雕塑的照片,陳列的目的是讓大家認識我的鐵雕的風格,由此可以了解我的「鶴」的造型特點。「鶴」的小型原作我從巴黎帶回來了,可惜此時放在北郊裡龍潭重機廠裡作放大的範樣,不能拿來陳列。
第二部分是詩。我十年來,陸陸續續寫了一些可以說是鄉愁的小詩,也可以說是以鄉愁作遊戲遣興題材的小詩。我曾在一篇小文裡說,我並不自以為是詩人,因為我並不刻意寫詩,只讓詩來找我。「教中文」、「展覽會」都是這樣寫成的。這一組小詩更是如此。李白的「靜夜思」是我們小時學背的第一首詩,老大之後,它在記憶裡要時常浮現,頑固而刁詭,我於是把散句織入我的詩中,它們也就在我的小詩中蔓生,或是引子、或是間架、或是疊唱……有點像西方立體派畫家剪下舊報紙、香煙盒貼入畫面,這裡把「靜夜思」剪成碎片,穿插到詩中,組成新的圖案。
第三部分是五幅水墨畫。我知道一個展覽會只展出文字是不夠的,只有文字,即使是詩,也容易使觀眾疲勞。用宣紙寫了詩之後,我約兩個姪女到昆明近郊去散步。由於近年的積極建設,城的邊緣到處是工地,幸好再走出去,還有菜地、村落。各種不同的蔬菜瓜豆一片一片構成錦繪,雲南特有的很高很大,姿態很別緻的尤加利樹在遠處疏疏地排列著。我覺得十分熟悉親切,作了些速寫。回家用水墨改畫在大幅宣紙上。這些畫不講究皴法、渲法,也不學現代派的浪潑墨。我感到當前中國水墨有兩極化的傾向,或者仍是筆筆有來歷的傳統水墨;或是受西方現代抽象影響的放肆的潑灑,我想用水墨和宣紙樸實地、笨拙地畫出我對故鄉的感受。我並不以為這已是成功的作品,在這意義下,我也不自以為是畫家。在一個星期之中,要掌握好一種工具,深入地認識一種題材、凝聚一種感受、形成一個風格,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會看畫的人,我想,自會窺出我的意圖,並判斷我究竟成功了多少。
年輕時代我也曾夢想把故鄉的岩石鑿打成雕刻。現在四十年過去了,我的雕刻材料主要是金屬,偶然也打過法國的砂岩、瑞士山澗裡的鵝卵,我和故鄉的岩石可能此生無緣了。不過,我想,至少要邀請一塊故鄉的石頭來參加展覽,這就是為什麼大家在進口處看到一塊青色大石。我或者應該用鐵鑽鑿幾條刻痕吧?或者用鮮明的顏料染成幾個符記吧?我應該用綳帶把它包紮起來吧?我應該把它剖成兩半,讓人看它的心子吧?……然而我終於沒有動它,我似乎沒有權力改變它,我的三姪婿把它從圓通山抱來,這樣完整地放在一個雕刻木座上。
最後,展覽會裡還展出了幾幅瑞士風景的水彩,大家也許覺得奇怪,為什麼它們出現在這裡。那是我妻子的作品。她是蘇黎世人。蘇黎世和昆明結成姊妹城了。她原姓裴斯大洛奇(Pestalozzi),和瑞士十八世紀大教育家裴斯大洛奇同一家族。在蘇城美術學校畢業之後,她到巴黎學畫和雕刻。一九五二年結婚,她繼續研究兒童繪畫教育,熱心社會事業,關心反戰、反核、反污染,支援第三世界,是一個天生的綠黨人。這也是繼承了瑞士人的傳統,對大自然有極強烈的愛,和中國人欣賞大自然的方式是很不同的。直到現在她仍去攀登阿爾卑斯的雪峰,跳到雪峰下的冰川湖裡游泳。兒子們慶祝她的六十歲時,她修正說:「第三個二十歲」。然而她懷念瑞士了。在法國三十年的生活使她仍然不能適應法國人的社會,和一個中國人生活三十年,她究竟嚮往另一個終極的歸宿。六十歲的時候,她回到瑞士,住在距蘇城三十公里的鄉村杜思屯(Dürstelen)。二十多年前我們在那裡買了一棟房子、一角森林、一片菜園。那是一個極優美的丘陵地區,她畫了許多風景畫。我很歡喜這些風景水彩,她能很深入地描繪出這地區特有的韻味,怕只有懷了回歸心理的人才能領略得到,描繪得出。我懂得她的回歸心理,正像她懂得我的回歸心理。她的回歸不是我的回歸,然而,卻又是我的回歸的一部分。通過她,這些牧場、杉林,對我,也依稀地瀰散著「故鄉」的芬味。這就是為什麼這幾幅杜思屯風景出現在這裡的原因。
附記:關於展出一塊原樣的石頭,當時只是直覺地如此去做,在台北的展覽會上放了一杯水,這次的展覽會上放了一塊石。事後我終耿耿於懷,自問這樣做的理由,自問應該以怎樣的觀念去解說,同時也想了一下中國人與石頭的關係。商周甚少利用石質建造,沒有刻過巨像,和埃及人比較,區別是很大的。似乎打石頭製雕刻,把石頭取來,加以劇烈的變形是從希臘經印度傳進來。漢代霍去病墓上的石刻大量保留著石塊的原始樣態和意味,刻工尊重天然的造形,審慎而巧心地加工,無論線條或體積都渾然、龐然,含攝著大自然茫闊、厚重、漫汗的韻律;那是雕像,也是岩石、是山、是大地。魏晉唐的佛像是西方觀念的石像,當然與西方雕刻也仍有相異之處。宋代多泥塑和木雕,而石頭則直接從自然界移來,滌除泥沙,不加敲琢,立在庭園裡,供人欣賞其本然的肌理脈絡、陽光大氣風化的表膚、水火侵蝕的竅穴、苔蘚織出的斑駁花紋。中國畫以山水為主流,學山水先學畫石。石無定形,而石是山水綑縕的起點,天地鴻濛的粒子。這是帶有形而上學意義的造形原始單位,如何能加以破壞呢?現代的西方雕刻家也有放一塊石頭視為作品的了,但是他們展示出機器的鑽孔、電鋸的齒痕,或打光的平面,要把人為強制的加工手續在什麼地方點出來。
放一塊石頭,作為觀照的對象,這還是中國文化的傳統。西方也有賣石頭的舖店,但陳設的是水晶、瑪瑙、銅礦、錫礦------光色豔奇,燦爛奪目。中國人卻可以玩味一個樸素的形體。這一塊石更為樸素,沒有李漁所讚美的「透、漏、瘦」,也沒有劉熙載在「藝概」中說的:「怪石以醜為美,醜到極處便是美到極處。」它在美醜未成立之前。這是石濤所謂「太樸一散,而法立矣。法立於何?立於一畫」的那一個造端。它在這裡。是「這裡」的標記。它自有自己的性格、儀態。它是一個存在的實體和象徵。它是存在一個地方的證明和座標。搬動石頭的最古老的用意。
五、「回歸的塑造」的可能
幾年前,這樣一個展覽會是不可能的。我那時要想為故鄉做一件雕刻,也是不可能想像的。比較有現代風格的藝術品固然不為政策所容許,當時大多數人的欣賞心理也還不能接受。我的「鶴」帶有立體結構主義的造形觀念,是用許多直線切裁的鐵片所焊成,經過姚鍾華先生推薦,政協願意接受,已屬不易。在製作過程中,重機廠負責人表示他們很欣賞這鶴,他們以為這展翼起飛的姿態含有深遠的樂觀的蘊意,希望我能同意他們同時焊製兩件,一件放置在重機廠廠內的花園裡,甚至願意給我一定報酬。我感到欣慰,立即答應了,也謝絕了報酬。就在西方,到美術館看現代雕刻的,也有不少並非真正愛好,只是為趕時髦,像打聽股票的行情、來年女裙的款式。今天一個重機工廠的職工能有開放的胸襟,以敏感的心靈來欣賞我的作品,使我感到難名的高興。
今天各位來看這個展覽,一定更能帶著開放的胸襟、敏銳的眼光,因為諸位是從事藝術工作的。詩人大概會從詩的角度評詩、畫家會從畫的角度評畫、書法家會從書法的角度評字……我當然也願意聽他們專業性的批評,但是我方才說過,我不是詩人,我的畫是臨時的嘗試;雕刻呢,是一套照片和一塊璞石,……我究竟要人看什麼呢?現代藝術潮流中有「裝置藝術」、「地攤藝術」、「大地藝術」、「多媒體藝術」、「觀念藝術」……我屬於哪一派?我想不必去管命名,我希望觀眾會這樣說:
「好像沒有什麼技巧,又好像很有技巧。有一個意念直接地、誠實地、樸質地表達出來。」
「好像新,又並非空洞的荒誕;好像傳統,又並無框框。說土,其中有新的觀念;說洋,又帶著鄉土的氣息。」
「畫、字、詩……合起來,給人一個總的渾然的感覺。這裡有一個『回歸』的塑造」。
六、「多重疊合的回歸」
我以為這個展覽會在今天有可能也並不是偶然的,還有很多別的因素。
最近幾年來,中西文化比較是一個大家熱烈討論的題目。這個問題之所以能被重新提出來,需要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承認中國文化有其特色,我們不能把中國文化簡單地歸類為封建的、中古的、愚昧落後的……這是中國文化的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回歸」。
其次,西方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對於絕對自信的現代主義有批評、有檢討。在藝術領域裡不再叫喊燒掉羅浮宮;相反,對歷史有深的懷戀和嚮往,在建築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近年來法國國家美術館以及私人畫廊都展出了過去視為分文不值的學院派的繪畫,是又一方面的表現。在小說裡,大家覺得又可以編寫情節、刻畫人物了。這種種似乎也可以用「回歸」來描寫。這是西方文化的「回歸」。
在造形藝術上還有一種「回歸」現象,是觀念藝術所鼓吹的「回到生活」。藝術要重新發現其產生的起源,把藝術的萌生看得比完成的作品更為重要。我們要欣賞的不是加工的精緻、錘煉的周密、製成品的完美,而是動機的真誠、構思的獨特、靈感在原始狀態的動人。這是中國藝術傳統的特色。如果拿中國繪畫和西方繪畫作比較,顯然西方人更重視作品。西方繪畫所需要的勞動量很大,以米開蘭基羅的「最後的審判」;大衞.查克.路易的「拿破崙一世加冕圖」是突出的例子。中國繪畫更重視作者,作品之好壞取決於作者的精神,與所消耗勞力的多少無關。西方到了近代才逐漸把原有的觀念改變,到印象派,畫家才有一天畫成一幅的作品;到了觀念藝術,作品更逐步縮減、變質,被觀念與操作所代替。藝術溶入生活。藝術「回歸」到生活。
所以我說這一次「回歸的塑造」之所以可能,還因為恰遇到幾種不同「回歸」的會合點上。否則雖有回歸,亦終無法塑造;徒有塑造的意圖,也終無觀眾的同情,終不成對話。
七、對話
沒有對話,也就什麼都沒有。
所謂「故鄉」,固然指這一片土地,這經緯度上的山國、地質、氣候、鳥獸、五穀、花果(我的老家至少有兩種果子是我從未在別處見過的:「嬌桃」和「拐棗」)……但是更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生活在這裡的人,在這裡勞動、思考、苦樂、創造的人傑地靈。沒有他們,實在說,也就沒有「故鄉」。地本無名。沒有法國人,法國也就不成其為法國;沒有英國人,不列顛三島也就沒有意義。土地塑造了人,人也塑造著土地。
高中時代在路南,我們曾唱一支歌叫「山國的兒女們」。孔子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我們知道江南水國的人特別靈敏精明,是「智」的表現;而雲南這樣叢山裡的人顯得樸厚緩慢,我願這是「仁」的表現。我去看雲南女畫家劉自鳴,早年我們同在巴黎學藝術,這次她給我看她的近作,一再用的一個詞是「深沉」。她說:
「這張畫我不喜歡,不夠深沉。」
「我認為這張畫深沉些。」
「你認為這張畫夠深沉麼?」
她的畫在形體的刻劃上、色彩的調配上都傾向簡樸,但在簡樸中確含蓄著一種「深沉」。我以為是極可貴的,屬於人的秉賦,不是學得到的。
我在西方觀察歐洲女子,對瑞士人有一種偏愛。我自己的解釋是:她們也是山國的兒女。她們有一種獨特的品質,使我聯想到高山上的湖泊。瑞士是一個多山多湖的國家,我想諸位都有機會見過瑞士的風景圖片。高山上的湖很藍、很清澈、很深、很靜、很幽、很曲折,在雪山與杉林的環抱中儲渟著。沒有激烈的風暴,給人以和平而深沉、謙遜而堅毅的感覺。
回歸不只是回到一個經緯度上,而且是回到一個精神感情的氣氛中。在這裡有一個對話,不只是鄉音的問答,而且是鄉音之外的心之間的應對。我在國外看到描寫雲南的小說、詩、畫,我都曾受到奇異的震動。
八、尾聲
所以我開頭所講的那個故事並沒有完。兩個雅典人指著對方喊出:「你瘋了!」後來怎樣了呢?兩個人當然都各持己見,不被對方的嘲謔所動搖。老雅典人懷著載欣載奔的心駛向港內;年輕雅典人一無返顧,航向大海。過了片刻,兩個人都若有所悟,又同時向對方喊過去:
「願雅典娜翼護你!」
他們忽然領會到對方的心理,無論是遠離雅典的,或是回歸雅典的,都該受到祝福。
附記:我想把這次展覽會的資料也印成一本冊子,雲南出版社的負責人表示有困難。我也知道在大陸出書得通過層層批准,很不容易。在香港遇到李賢文先生,他立刻欣然說:這「回歸的塑造」在台灣出版正是時候,因為目前正在醞釀開放往大陸探親,這些詩一定會得到共鳴。想不到在許多回歸的會合中又能遇到這一回歸的浪潮。最近開放往大陸探親的決策,從計劃到公佈到實行,變化迅速,已在報上見到照片。那些到紅十字會登記的老年人,我的年紀的、比我更老的年紀的,傴僂了背伏在桌上填寫表格,看了令人心酸。我想他們有「初聞涕淚滿衣裳」的心情吧!「歸心如箭」吧!祝願他們都能如意地塑造自己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