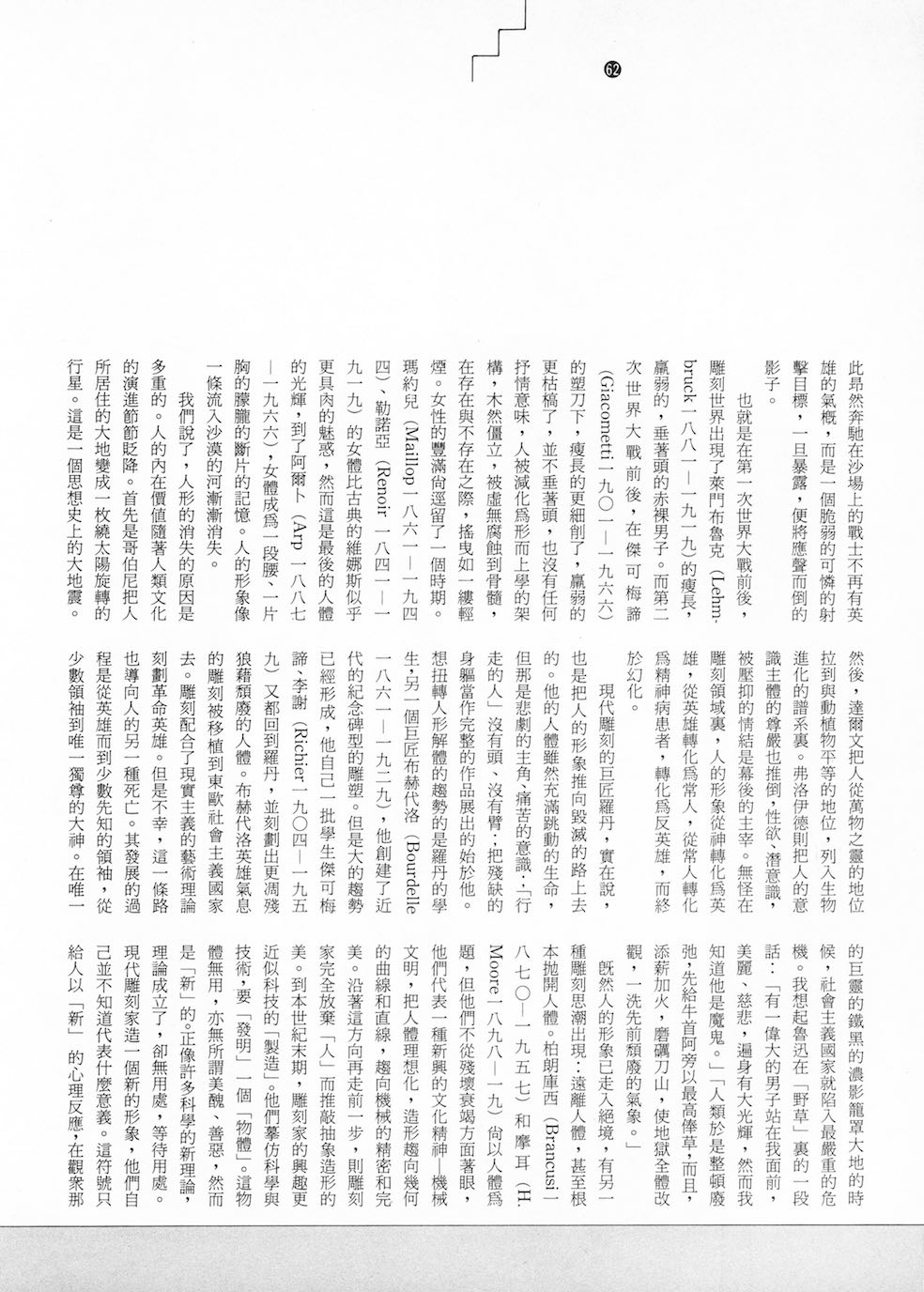奧運會的精神
漢城奧林匹克雕刻繪畫的目錄是一本五公斤重的巨型大畫冊,拿在手裡便彷彿捧著藝術史的一個里程碑。序言是這樣寫的:
「如果奧運會僅只是局限於體育競賽,那麼絕不會發展為今天這樣的具世界性的活動。奧運精神不只在錘鍊心身,而且亦通過藝術創造促進美的欣賞,通過學術研究開拓新知識,而這些活動的終極目的是為了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藝術活動具有一種神秘的力量,使人們越過語言的、種族的、意識形態的,以及政治的種種障礙而得到共同情感的溝通。為了這個理由,我們把漢城奧運會的文化意義著重地突出,組織了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次藝術奧林匹克。世界四隅的當代藝術作品將匯聚在這裡,這是一個稀有可貴的機會讓我們來欣賞這許多不同的可能。
從遠古,人類便在穴壁上作畫。我們屏息拭目,觀察人類將怎樣迎接,並表現二十一世紀。藝術是一個嚴肅的努力。我堅信藝術奧林匹克將激發對於人類的未來作深入的探詢;我誠懇地感謝為這一次藝術節的設計與實現付出勤勞與智慧的所有的人。
一九八八年八月漢城奧運會組織委員會主席朴世直」
文章中「世界和平」、「世界四隅」、「二十一世紀」……一連串的用詞顯得冠冕堂皇,陳義甚高,但是做為世界奧林匹克雕刻公園,和奧林匹克繪畫展覽的目錄的序言,大概也只能如此寫,似乎也應該如此寫吧。
雕刻公園實況
奧運會組織者邀請兩批雕刻家赴漢城,首批參加開幕儀式;第二批參加閉幕儀式。我因九月初剛從北京回巴黎,需要略作休息,所以參加了第二批,和王克平、陳啟耀兩位同行。這一批雕刻家共有三十人左右,來自法國、西德、意大利、西班牙、愛爾蘭、加拿大、美國、波蘭、蘇聯、烏拉圭、瓜地馬拉、墨西哥、阿根廷、委內瑞拉、多明尼加、埃及、摩洛哥、利比亞、伊朗、印度、印度尼西亞、泰國、新加坡、日本……真是來自「世界四隅」,濟濟一堂。
到漢城的次日,九月二十九,便被招待在雕刻公園大樓的最高層午餐。飯後參觀公園。不知道為什麼緣故,是什麼人的失職,我的作品未曾印入目錄。我問嚮導小姐:「你知道我的雕刻在哪裡嗎?」,她居然點頭說:「知道。」我頗有些懷疑,因為二百件作品,分散在這樣大的場地,按說很不容易記得的,非靠目錄尋索不可。她逕直帶我去,果然在一座中國式涼亭不遠的地方找到了我的「鐵鶴」。審視了自己的得失,拍了幾張照,也匆匆地看了一些別人的作品。
十月三日又到公園一次,看得比較仔細,費了約四小時,巡禮了一遍。其實也仍是很匆忙,仍不免有遺漏。因為從一座雕刻走到另一座有時相當遠,就以平均三分鐘看一件雕刻計算,二百件雕刻需時六百分鐘,也就是需要整整十小時。
我怎樣談我的觀感呢?很不容易說。
此刻回想雕刻公園,最先浮現的是那一片廣闊、舒適的大空間:上邊是勻淨高爽的藍色秋空,下邊是軟軟延展的大地,草坪連綿,緩緩起伏;幾波隆起的小丘陵,繞著幾灣粼粼的池水;新植的林木還有些怯懦。「公園」的氣氛和平而溫柔,太陽的光度很強,但並不刺眼,空氣的溫度使皮膚感到清醒而快意,那是競技的理想的溫度,我們自己也想要換上輕衫短褲,跑一跑,跳一跳。
然而,回想那裡的雕刻,卻引起胸肌的壓抑、不自在。這裡、那裡,巨大而怪異的形體散佈在草坪上,木的、石的、金屬的、水泥的……我們難於描寫,難於歸類,只感到視覺受到侵犯、暴虐。並且,勻淨的天空,明朗的陽光、清新的空氣、草坪、小樹也都遭受到侵犯與暴虐。
那一片廣闊坦蕩的大地像一個精美的托盤,我們挑選了最優良的產品陳列在這裡,那上面神秘的藍天似乎會有外星客的來到。可是這些產品真是足以代表人類今天的藝術成就麼?反映這時代的精神面貌麼?外星客會怎樣評價呢?二千五百年前古希臘人又會怎樣評價呢?我們不是把這公園命名作「奧林匹克」麼?造阿波羅的希臘雕刻家會說什麼?我們不是把陳列在這公園裡的作品保存下去麼?二十一世紀的來者又將怎樣評價?
且不說古人、來者,以及外星人,我們自己先茫惑了,我自己先茫惑了。
從人體到物體
希臘時代的雕刻是「人體」的讚歌,讚美競技的優勝者,讚美比競技者更完美的神的軀體:阿波羅、維娜斯……今天,在這裡豎起的雕刻,以人體為主題的不及二十件,也就是說不到十分之一,而這十分之一的作品是人形的殘片或廢墟。其餘的是什麼呢?我想可以總稱作「物體」吧。因為「抽象雕刻」一辭也並不恰當,有些分明是一把椅子、一堵牆、一架機器……從希臘到今天雕刻的演變,扼要地說,大概是從「人體」到了「物體」。
比我們的肉軀更美妙的,不再是阿波羅、維娜斯,而是「蘋果」、「蝨子」、「老鼠」…這些電腦的構件。「阿波羅」已成為太空飛箭的名字。二十世紀人類所製造的東西遠遠超過人的雙臂的膂力、兩眼的視能、兩耳的聽覺……這肉軀的貶值過程是逐步的,原因是多種的,但是如果要指派一個象徵性的日子,那麼也許可以說是一九一六年的九月十五日。那一天在法國北部英軍防線上衝出來坦克車,從此昂然奔馳在沙場上的戰士不再有英雄的氣概,而是一個脆弱的可憐的射擊目標,一旦暴露,便將應聲而倒的影子。
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雕刻世界出現了萊門布魯克(Lehmbruck 一八八一—一九一九)的瘦長,羸弱的,垂著頭的赤裸男子。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在傑可梅諦(Giacometti 一九〇一—一九六六)的塑刀下,瘦長的更細削了,羸弱的更枯槁了,並不垂著頭,也沒有任何抒情意味,人被減化為形而上學的架構,木然僵立,被虛無腐蝕到骨髓,在存在與不存在之際,搖曳如一縷輕煙。女性的豐滿尚逕留了一個時期。瑪約兒(Maillop 一八六一—一九四四)、勒諾亞(Renoir 一八四一—一九一九)的女體比古典的維娜斯似乎更具肉的魅惑,然而這是最後的人體的光輝,到了阿爾卜(Arp 一八八七—一九六六),女體成為一段腰、一片胸的朦朧的斷片的記憶。人的形象像一條流入沙漠的河漸漸消失。
我們說了,人形的消失的原因是多重的。人的內在價值隨著人類文化的演進節節貶降。首先是哥伯尼把人所居住的大地變成一枚繞太陽旋轉的行星。這是一個思想史上的大地震。然後,達爾文把人從萬物之靈的地位拉到與動植物平等的地位,列入生物進化的譜系裡。弗洛伊德則把人的意識主體的尊嚴也推倒,性欲、潛意識,被壓抑的情結是幕後的主宰。無怪在雕刻領域裡,人的形象從神轉化為英雄,從英雄轉化為常人,從常人轉化為精神病患者,轉化為反英雄,而終於幻化。
現代雕刻的巨匠羅丹,實在說,也是把人的形象推向毀滅的路上去的。他的人體雖然充滿跳動的生命,但那是悲劇的主角、痛苦的意識;「行走的人」沒有頭、沒有臂;把殘缺的身軀當作完整的作品展出的始於他。想扭轉人形解體的趨勢的是羅丹的學生,另一個巨匠布赫代洛(Bourdelle 一八六一—一九二九),他創建了近代的紀念碑型的雕塑。但是大的趨勢已經形成,他自己一批學生傑可梅諦、李謝(Richier 一九〇四—一九五九)又都回到羅丹,並刻劃出更凋殘狼藉頹廢的人體。布赫代洛英雄氣息的雕刻被移植到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去。雕刻配合了現實主義的藝術理論刻劃革命英雄。但是不幸,這一條路也導向人的另一種死亡。其發展的過程是從英雄而到少數先知的領袖,從少數領袖到唯一獨尊的大神。在唯一的巨靈的鐵黑的濃影籠罩大地的時候,社會主義國家就陷入最嚴重的危機。我想起魯迅在「野草」裡的一段話:「有一偉大的男子站在我面前,美麗、慈悲,遍身有大光輝,然而我知道他是魔鬼。」「人類於是整頓廢弛,先給牛首阿旁以最高俸草,而且,添薪加火,磨礪刀山,使地獄全體改觀,一洗先前頹廢的氣象。」
既然人的形象已走入絕境,有另一種雕刻思潮出現:遠離人體,甚至根本拋開人體。柏朗庫西(Brancusi 一八七〇—一九五七)和摩耳(H. Moore 一八九八—一九八六)尚以人體為題,但他們不從殘壞衰竭方面著眼,他們代表一種新興的文化精神—機械文明,把人體理想化,造形趨向幾何的曲線和直線,趨向機械的精密和完美。沿著這方向再走前一步,則雕刻家完全放棄「人」而推敲抽象造形的美。到本世紀末期,雕刻家的興趣更近似科技的「製造」。他們摹仿科學與技術,要「發明」一個「物體」。這物體無用,亦無所謂美醜、善惡,然而是「新」的。正像許多科學的新理論,理論成立了,卻無用處,等待用處。現代雕刻家造一個新的形象,他們自己並不知道代表什麼意義。這符號只給人以「新」的心理反應,在觀眾那裡激起無可名的好奇和驚怖。這是一個謎,而他們不知道謎底。那是沒有謎底的謎,或者說那謎本身就是謎底。如果要他們解釋自己的作品,有的會寫出一套和形體同樣令人眩惑的充滿玄學氣息、語言魔術的議論;有的則天真而得意地說:「我不知道」。藝術家不需要說話。藝術品不需要說明。於是自有精神分析家來尋索情結的根源;有藝評家用語言學、哲學的術語來詮譯;有藝術史家來排比、歸類。一旦被歸類、被定名、輸入電腦,作品也就失掉新奇,藝術家又要走向更新的領域去。
雕塑的分類
用「人體」和「物體」的觀念來觀察雕刻公園裡的作品,也許可以分做以下幾類:
屬於「人體」的雕刻有三類:
一、殘破的。像蘇聯人貝爾林(Leonid Berlin)的「為什麼?」這是用廢鐵焊接的人物,面目模糊,兩臂伸開,兩手張著,好像在仰天詢問。
二、缺損的。這一類和前一類不同,整體有所缺少,但並不殘破,人類本身的刻畫的古典手法很寫實、很細緻,但以現代觀念把完整的形體加以打缺。例如阿爾及利亞人阿瑪拉(Amara)和西班牙人貝洛卡(Berrocal)的石刻,兩人都做了青年人的像,都同樣把頭的上半部削去。前者做的是兩個胸像,被故意拆裂做幾段。後者做的是個著衣的身軀,膝以下的部分也被削去。凱撒(Cesar)的「大姆指」也可以放在這一類。
三、稚拙的。手法笨拙,雕像如玩偶。例如捷克人讓可維奇(Jankovic)的「優勝者」。一個上半身,連接著三個並排的下半身。他自說是嘲諷競爭,每個人都想得第一名,但第一名只有一個。
非人體的雕刻也有三類:
一、抽象雕刻。這是傳統雕刻的延續,但是把寫實的意圖排除。基座上放置一個完整的形體,雕刻家著眼於幾何結構的完美。例如巴西人德.卡瑪哥(De Camargo),秘魯人古茲曼(Guzman)的作品。抽象大型紀念碑也屬於這一類,像韓國的(Moon Shin)的聯珠狀巨柱。這是公園中最高,最令人注目的標誌物。
二、場景雕刻。把雕刻基座取消,把單體形象打破,化成多數形體,把場地佈置的觀念引入,把建築空間的觀念引入。如以色列人卡拉旺(Karavan)的「日晷」。據稱是獻給 Sejong 王的。那是十二株六公尺高的木柱,每株縱剖為二,兩半相距約半公尺,形成一條狹窄的廊道。距這一排大柱約十公尺的南北兩邊還各立著一對這樣的半圓柱。
三、喻意物體。既然不是純粹的抽象造形,那就是一個可以叫得出名字的東西,或者可以叫得出名字,或者簡直就是那東西的複製。例如古巴的布里脫.阿維拉娜(Brito-Avellana)的椅子和門,題為「內省:童年記憶」。阿根廷的瑪勒(Maler)排列了大大小小的十來把椅子凳子,還有一個扁平的曲卷的人形。在現代,椅子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現代戲劇裡、現代舞蹈裡往往是唯一的道具。在雕刻公園,以椅子為主題的作品有四座。美國人萊維特(Lewitt)的「立方體之一角」是以直角相接的兩段短牆。波蘭人卡立那(Kalina)的「一路平安」是一段鐵軌,放置了五對火車輪。第一對是完整的,第二對有一部分陷入軌中,依次愈陷愈深,第五對只剩下小小的弧形。
這樣的分類當然並非界線分明的,像荷蘭人布魯斯(Brusse)的「狗的生活」,既用了喻意物體,又有場景觀念。他組合了高牆、方窗、石級、鐵鍊…效果很像舞台的佈景。
這樣的分類對雕刻的欣賞,實在說,恐怕並沒有什麼幫助。分類之議,給每件雕刻一個位置,使觀者對雕刻有些理性的知識,不致於瞠目結舌,張惶失措,但並不一定引起他對作品的欣賞,更不一定造成對作品的喜愛。
我們似乎聽到惡魔的笑聲
就雕刻家自己走在這裡,也會感到迷惑的。對「雕刻」,每個雕刻家有他自己所給的定義;每個雕刻家苦心摩挲他所膜拜的形體,或者掘出他在潛意識底層所溫孵的怪卵。
雕刻家們似乎在佈置一個大規模的祭典。從世界五洲的各個角落來了多種部族的代表,在這裡豎起奇奇怪怪的圖騰,展開機械的,塊狀的符咒,擺佈出難以辨認的面具。我們用怪異的聲音祈禱,以荒誕的語言召喚神祇的到來。然而是怎樣的神祇呢?沒有名稱。也許只能是撒旦吧。而這些圖騰與符咒的製造者並沒有受到任何巫師、教主、修士的指示;他們只是被不可知的誘惑所蠱動,被無限的嘗試所支使,被永不能滿足的好奇所催逼,他們各以為是藝術的忠僕、又是藝術的叛徒。他們是探險家。每個人都是和梅菲斯托弗列斯答約的浮士德,他要追求,無所禁忌,徹底自由,一切都是被允許的,不再有罪與惡,美與醜,正與邪,意義與無意義,這樣的出軌、犯規是令人心驚膽戰的,但他既已用鑰匙啟開了禁止的門了,他只得前去。他有大恐懼,但在這恐懼中摻有好奇的自虐的快意,邪凟與觸犯帶來壞孩子狡黠的滿足。他要發現新的疆界,發現新的大陸,或者島嶼或者岩礁,冰山,甚至海市蜃樓也好。
我們要到哪裡去?沒有人能回答。你問雕刻家:「你到底要幹什麼?」絕大多數會說:「我不知道,我在找。」
我們似乎聽到惡魔的笑聲。
創作的沈思
而我是並不相信惡魔的。我自以為生長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既不懼怕惡魔,也不慕戀天使。中國文化沒有神學,也沒有上帝與魔鬼的故事。我徘徊在奧林匹克雕刻公園,心底應該是平靜的,在這些離奇的造形之林間,可以泰然地漫步。
中國文化裡早已存在超越美與醜、善與惡的美學。儒家提出盡善盡美的標準後(論語.八佾:「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道家便提出反對的意見,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莊子說得更具體:「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齊物論)「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地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北游)如果莊子是雕刻家,他會做出膚肌若冰雪的處子,也會做出猙獰醜怪的人物,「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而且他不會局限於塑造人的形象:「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大宗師),他可以冶製大鵬、蝴蝶、鴟鴞…風與渾沌,以及純粹的觀念藝術,他說:「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雖我無成,亦可謂成矣。」(齊物論)
從大自然懷中取一塊怪石立在庭園裡,觀賞它的透漏譎詭,不是中國的傳統嗎?(所以王克平可以送去一段大木椿)
我徘徊在那一片軟軟的草坪上,我以為我可以輕鬆地步去,怡然、逍遙,有莊周的眼光、天地的心。我可以有寬闊的胸懷去接近每一件作品。「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齊物論)
然而,很快我就發現這樣的心態並不容易保持。有的作品,我可以同情地體味;有的作品令我漠然;有的作品,我始終不能接受,我看了不舒服,像吃了不能消化的食物,積梗在胸口。「聖人無己」,而我不能,我只是我自己,只能以我的眼睛去觀測。如果真是以接受一切的態度去欣賞,其實也就沒有了欣賞。荀子說了:「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我於是想,以我這樣的心理尚且遇到欣賞的局限,其他的觀者必有更嚴重的偏見與偏好吧。我又想:我自己的作品放在這裡,會被怎樣看待呢?二十根鋼條,瘦硬的直線,架搭焊接起來,在晴空中支成鶴的簡形—我自己認為是多年提煉成的形式,並且在我之前,中國文化裡醞釀著這樣的形式,不過我同時採用了西方某些抽象雕刻的手法。我在打製的時候,確經驗到很大的愉快,測定這些鋼條的長短,傾斜的角度,調準它們的輻奏疏密,比例節奏,製作凝聚的感覺,上升的感覺,超驗意象的暗示。但是不能領會我的意圖的人大概只看見幾根灰黑冰冷的鐵桿,他們會憤憤然,哀歎雕刻的沒落。
藝術品是一個矛盾的結合體,它要使人們有感情的溝通,(如奧林匹克雕刻繪畫目錄序言所說的)又在尋找感情的密碼,顯示感情溝通的不易。
三四個年輕中學女生走過,擁在我的鐵雕下拍照,笑著、嚷著,又一群更年輕的學生跑過來了,擁著拍照,笑著、嚷著。
我想她們才是真正的欣賞者吧。她們不提什麼問題,沒有什麼懷疑。對她們說,這些就叫作「雕刻」。而她們欣然接受,而雕刻也欣然裝飾了她們的生活。
我不懂韓文,無法和她們交談,只看到她們的健康快活的面龐上沒有一絲陰影。人類文化處在一個開拓與發現的時代,我們已躍出地球,進入星際,同時我們也進入微觀宇宙的探險,進入心理世界,生物化學世界的探險,我們時時得準備新視野的展現,接受新的驚愕。藝術家不斷逃出過去的範疇,找新的結構、「新的戰慄」。我們在自己所製造的精神失重中不能適應,發生恐懼、感到惶惑,而這些孩子似乎無憂無慮,欣然在這些新現象、新形象中長大起來。我們臨時的橋頭陣地,在她們是已經征服了的根據地,要更向前面進發了。
我們的作品已經留在那一片草坪上,對於未來者說,我們的憂慮,以及因這憂慮而說的許多話,怕都是多餘的了。
(此文內小標題由本刊代擬)